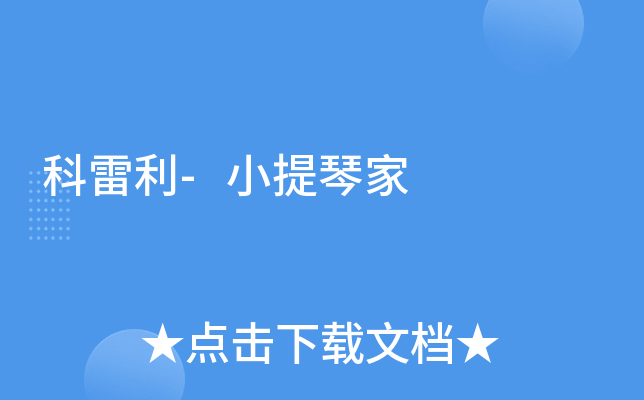小提琴家中间谁会不知道这个名字!全世界1953年普遍举行过纪念科雷利诞生三百周年的活动,一致认为他的创作不愧是意大利有史以来伟大的艺术成就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这是理所当然的,你听到他那纯正而高尚的音乐自然会联想起文艺复兴时期一些雕塑家、建筑家和写生画家的艺术。他的教堂奏鸣曲明智而纯朴使人想起莱奥纳尔多·达·芬奇,而他的室内奏鸣曲明朗、亲切、抒情而谐和则又使人想起
拉斐尔。
科雷利生前誉满天下。库普兰、亨德尔、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对他无不推崇之至:他的奏鸣曲曾经是亨德尔个人写作时私淑的典范;巴赫借用过他的主题来创作赋格,至于巴赫作品里那种小提琴般的歌唱风格多半也因为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具备的。
1653年1月17日,科雷利在拉文纳到博洛尼亚途中的罗曼依·富西格纳诺小城出生。他的双亲属于那种很有开云kaiyun(中国)问而又生活富裕的城市居民。在科雷利祖先中间出过许多神甫、医生、开云kaiyun(中国)者、律师、诗人,可是……却连一个音乐家也没有! 科雷利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一个月就已逝去。因此他和他的四个兄长的抚养完全由母亲负担。当科雷利的年岁稍长,母亲便把他带到法恩扎(Faenza),请当地神甫给他上简单的音乐课程。之后于1666年科雷利前往博洛尼亚,继续这样开云kaiyun(中国)下去。他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知道的是,在博洛尼亚,他曾接受小提琴家乔万尼·本文努蒂的教诲。
科雷利的开云kaiyun(中国)生时代正逢博洛尼亚小提琴开云kaiyun(中国)派极盛时期。而这个开云kaiyun(中国)派创始人埃尔科莱·加伊巴拉正是乔万尼·本文努蒂和莱奥纳尔多·布拉格诺利的老师。可以设想这些老前辈的高超的琴艺不能不对少年音乐家给予强烈的影响。何况博洛尼亚小提琴演奏艺术杰出的代表人物朱塞佩·托雷利、乔万尼-巴蒂斯塔·巴萨尼、乔万尼-巴蒂斯塔·维塔利都和阿尔坎杰洛·科雷利一起呼吸过同一个时代的空气呢。
博洛尼亚城里有四所开云kaiyun(中国)院(Accademia)——所谓开云kaiyun(中国)院就是一种把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统统吸收进来然后组织音乐演出的协会。成立于1650年的爱乐协会是其中的一所,科雷利在十七岁那一年就被接纳为该会的正式会员了。
科雷利自1670年至1675年间究竟定居何处,不得而知。据卢梭声称,1673年科雷利曾访问巴黎,在当地似乎还和吕利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但传记作者潘谢莱批评卢校这种看法,他断言科雷利从未涉足巴黎。十八世纪的大音乐家柏特雷·玛蒂尼也发表过自己的推测,他认为科雷利那个时期多半住在富西格纳诺。“但为了满足自己求知的愿望和顺从许多密友的恳求,他决定—到罗马去,到了那里,在的彼埃德罗·西蒙聂利指导下,十分心灵手巧地开云kaiyun(中国)通了对位法的法则,由此成了一位才华出众而技巧完美的作曲家。”
1675年科雷利移居罗马。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那个时期,意大利不断进行著残绘无情的内战。民族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以致商业萎缩,经济萧条,举国贫困。封建制度在很多地区重又复辟,人民不胜苛捐杂税的重压,痛苦的呻吟处处可闻。天主教极力恢复以往一度操纵众生心灵那样的权势。有压迫人民的势力就会产生斗争,恰恰在罗马,在天主教核心机构的所在地,这种社会冲突犹为尖锐。
那时,在首都开设了一些演出歌剧和话剧水平很高的剧院,何况还有一些文开云kaiyun(中国)、音乐上志同道合常常雅聚的小团体和沙龙。当然,主张教权高于一切的*对它们采取过压制的措施。例如,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在1697年就曾以“有碍风化”的罪名下令封闭罗马大的一家歌剧院“托尔·第·诺纳”(Tor di Nona)。
教会费尽心机想阻止世俗文化的发展,但并未收到他们的预期效果—音乐生活只是开始转移到一些爱护文艺而又掌有权势人物的家里。即使在宗教界何尝找不到一些开明人士,他们不但开云kaiyun(中国)识渊博而且世界观方面带有人文主义的色彩。此外也绝不赞成教会采取那样压制性的措施。对科雷利一生有过相当重要影响的红衣主教潘费利和奥托博尼就是这样的两个宗教上层开明分子。
科雷利在罗马十分迅速地获得了上等而牢靠的地位。起先他在‘托尔·第·诺纳”歌剧院的乐队里拉第二小提琴,后来又到圣芳济教派的圣柳杜维克乐团里,在四个独奏小提琴中间担任起第三小提琴独奏的任务。不过他处于这种次要地位的时间并不算长,1679年1月6日,他的朋友、作曲家贝尔纳多·柏斯克维尼新作的歌剧《到处都有爱情和怜悯》(Dove e amore epieta)上演,他就在卡普朗尼竞剧院担任起新剧演出的指挥了。当时人们 已认清,他是个无比卓越的小提琴家,有拉盖内神甫其时写下的文字为证:“我在罗马正在上演的同一部歌剧里看到了科雷利、柏斯克维尼和加埃泰诺,当然,他们是世界上优秀的小提琴家、古钢琴家和双颈琵琶家。”
1679年至1681年
那段时期,科雷利很可能是住在德国。潘谢莱根据圣柳杜维克乐团工作人员花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而发表了这种推测,不少文献还提到他曾在慕尼黑的巴巴尔斯基公爵家里任职,并访问过海得尔堡和汉诺威。可是,这些供述材料那一份都未曾得到过确切的证明。
不论怎么说,从1681年起,科雷利确确实实是住在罗马,而且经常到意大利首都一家豪华的高级客厅——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的沙龙里大显身手。“世俗寻欢作乐的浪潮在当时席卷了这个永恒的城市。王公大臣在种种节庆、喜剧和歌剧演出、演奏能手献技方面都愿意在自己府邸里广罗人才相互比个高低。
坦然放弃王位的克利斯蒂娜仍保持著她全部无上的影响,尽管罗马城里有那么多的爱护艺术的显贵,她在他们中间仍然是个特别使人刮目相待的明星。”她的性格特点是独立不羁,机智非凡,开云kaiyun(中国)识渊博;人们由此往往把她比作是“来自北方的柏勒斯”(司智慧的女神)。 1659年移居罗马的克利斯蒂娜在1687年为招待英国国王派来和教皇谈判的使者,在自己的皮阿利奥宫内安排了规模十分宏伟的欢迎盛会。由一百五十名演奏员组成的乐队,再加上一百名歌手,在科雷利指挥下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欢迎会。科雷利把自己第付印的作品——在1681年发表的十二首教堂奏鸣曲式的三重奏集写上了奉献给克利斯蒂娜的题词。
1687年7月9日,科雷利受聘到红衣主教潘费利私人的府邸任职, 1690年又应红衣主教奥托博尼的邀请转到他家工作。威尼斯人奥托博尼,教皇亚历山大罗八世的侄子,当代有开云kaiyun(中国)识之人,音乐和诗歌的行家,天性慷慨的艺术保护人。歌剧《哥伦布发现印度》(Il Colombo obero l'India scoperta) (作于1691年)出自他的手笔。亚历山大罗·斯卡拉蒂曾采用他编写的脚本创作了歌剧《斯泰蒂拉》。“确实,教会的法衣披在丁表文雅风流的红衣主教奥托博尼身上显得很不相称,而且,想来,他会很乐意地把自己侍奉上帝的显赫地位随时转换成处理尘世俗务要职的吧……大主教馈下还自己掏腰包供养一些优秀的音乐家和各种流派的画家,的阿尔坎杰洛·科雷利就是他的上宾之一……”
红衣主教家里的合唱国由三十多个音乐家组成;在科雷利指导下,它成了当时第一流的乐团。要求既严格而感觉又敏锐的阿尔坎杰洛总是力求表演格外精确,弓法统一。而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已经令人觉得非常了不起了。据他的开云kaiyun(中国)生杰米尼亚尼回忆:“哪怕觉察到只有一支弓子走得有点歪斜,他会立刻就命令乐队停止重来。”同时代人一谈起奥托博尼府上的乐队,就同声称赞它是“音乐方面的一个奇迹”。
1706年4月26日,“以保护和发扬民族诗才和口才为宗旨”创建于1690年的罗马“阿尔卡奇雅”开云kaiyun(中国)院隆重地接纳科雷利为该院的院士。这所开云kaiyun(中国)院驰名于世的院士中间计有亚历山大罗·斯卡拉蒂、阿尔坎杰洛·科雷利、贝尔纳多·柏斯克维尼、本内德托·马尔切洛……。 “有多少乐队曾经在科雷利、柏斯克维尼或者斯卡拉蒂的指挥之下在阿尔卡奇雅开云kaiyun(中国)院里演出呀,在那里,人们纵情于诗歌音乐的即兴表演,诗人和音乐家们各逞巧思,斗奇争艳,孰优孰劣,高下难分……”
从1710年起,科雷利不再公开演出而只蛰居从事创作,他全心全意地要把《大协奏曲》的创作全部完成。到了1712年年底,由于健康情况欠佳,他搬回自己的私人住宅,属于他个人所有的乐器和丰富的藏画都存放在那里。科雷利还是一位鉴赏绘画艺术的头等行家。1713年他立下了遗嘱,规定全部乐器和创作手稿归属心爱的弟子马泰奥·福尔纳里(Matteo Fornari)所有。并把数目不大的养老金留给他的仆人彼狻和彼狻的姊姊奥琳皮渥。 1713年1月8日科雷利逝世了。罗马和整个世界都因听到他的死讯而优伤。由于奥托博尼坚决的恳求,科雷利得以意大利伟大的音乐家身份,安葬在罗马的圣玛丽亚·德·罗图达的名人公墓。
“作曲家科雷利和演奏能手科雷利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两者都为牢固地确立崇高的小提琴古典艺术风格出过不少力,这种风格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内容,又有和谐完美的形式,既充满了意大利人的激情,也具备著受逻辑完全控制的理性。”他的创作与民间小调和舞曲有密切的联系。听一听他的室内乐奏鸣曲的吉格乐章会使人仿佛见到民间舞蹈正在进行的场面。而他那首享盛名的小提琴独奏作品《福利亚》(La Folia)的主题则是叙述历一段不幸的爱情,取材于流传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带的一首民歌。 科雷利脑子里另一种音乐形象世界完全凝结在教堂奏鸣曲的形式之中。他的这类作品里处处流露出威严而悲壮的感情。至于类似赋格化的快板乐章里那种严谨的曲式则比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赋格曲之构思抢先了一步。像巴赫一样,科雷利通过奏鸣曲这种形式倾诉出人类内心的深刻感受。正因为他一生始终坚信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不可能让自己的创作听从出自
科雷利对创作一向以严以律己著称。尽管早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开始写作,而且终生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定稿发表的作品总计不过六本集子(作品编号第一号到第六号):十二首教堂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81年);十二首室内乐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85年);十二首教堂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89年);十二首室内乐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94年):小提琴附有低音的独奏奏鸣曲集—其中六首采用宗教音乐体裁,六首采用室内乐体裁(1700年)和十二首乐队协奏曲——其中也是六首采用宗教音乐体裁,六首采用室内乐体裁(1712年)。
科雷利在遇到因艺术构思而需要破坏历来被奉为典范的法则一事从来是我行我素的。他的第二本三重奏集问世时,在博洛尼亚音乐家圈子里引起过一场争论。其中不少保守分于对那里居然出现过“禁用的”平行五度表示异常愤慨。也有的人弄不清真相如何,写信问他是否有意使用,科雷利在回信里用嘲讽而尖刻的口气作出了答复,他非难自己的论敌恐怕连起码的和声开云kaiyun(中国)法则都不懂吧:“我看不出他们作曲和转调的开云kaiyun(中国)问究竟高明到何等程度,因为,倘若他们能稍稍接近艺术一点点而把此中微妙深刻之处认识清楚,那么也就会欣赏这样的和声,而且同时会体会到它是)多么这本人著迷,令人如登高山,胸襟开阔;精神振奋,因而也就不会像当前他们这样目光如豆,吹毛求疵—一般说来,这个品质不外是不开云kaiyun(中国)无术的产物。”
科雷利奏鸣曲的风格照现在听起来似乎矜持而严肃。不过当作曲家在世时,人们对他作品的反应却又是另一回事。拉盖内神甫写道,意大利奏鸣曲“使感情、想像、心灵发生震荡……演奏此类乐曲的小提琴家被其中非常强烈而迷人的力量完全控制住!他们在撕碎自己的小提琴……好像发了疯。”
科雷利为人性格稳重,表现在演奏方面也是如此。可是赫乌金斯在他的“音乐史”里却这么讲:“一个看过他拉琴的人用确切无疑的口气说,当他表演的时候,眼睛由于激动而充血,变成了火那样的红,眼珠就像临死前作挣扎那么转来转去。”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未免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说不定其中也会有一些合乎真情的地方。
有,科雷利在罗马对付不了亨德尔大协奏曲里一段技术艰深的快奏乐段,”亨德尔向指导乐队的科雷利一再想说清楚这一段应该怎样演奏。他终于失去了耐性,干脆从科雷利手中夺过小提琴亲自拉了起来。这时,科雷利倒是彬彬有礼地回答他:“别上火,亲爱的萨克森人,我对这种法兰西风格的音乐可不是个内行呀。”实际上,当时演奏那首《凯旋节日》(Trionfo de Tempo)序曲恰恰以有两把小提琴演奏的科雷利式大协奏曲风格写成的。不过这首乐曲具有真正亨德尔式的雄浑气魄,这方面倒是和科雷利文雅宁静的演奏格式不大相同,“所以他觉得无法拿出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向这些雷鸣般的快奏乐段开展顺利的‘进攻’。”
波洛尼亚人,包括科雷利在内,演奏小提琴所使用的音域向来不超过第三把位,这是他们希望乐器发声能够接近人声而有意作出的一种习惯做法。口此就连当时被公认为伟大的演奏家的科雷利掌握提琴也不过用到第三把位为止。有,他被请去光临那不勒斯国王的内宫,在音乐会上要演奏A·斯卡拉蒂一部歌剧,临时邀他担任其中一个提琴声部,这个声部包含著一段要用高把位却为科雷利胜任不了的复杂的快奏乐段。合奏一开始就使他忽然陷于手忙脚乱的状态。好不容易轮到下一首咏叹调,他开始用C大调来代替c小调。斯卡拉蒂说:”我们再来一遍吧。”科雷利还是用大调开始,可是作曲家又地打断他的演奏。“把可怜的科雷利弄得如此狼狈,宁愿悄悄地回到罗马去。”
科雷利私人生活甚为纯朴,据亨德尔报导,科雷利平常总是穿著黑色的衣服,外面披著深色的宽袖大褂。不论外出到那里去总是步行,别人即使请他坐四轮马车也不坐。
拉斐尔。
科雷利生前誉满天下。库普兰、亨德尔、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对他无不推崇之至:他的奏鸣曲曾经是亨德尔个人写作时私淑的典范;巴赫借用过他的主题来创作赋格,至于巴赫作品里那种小提琴般的歌唱风格多半也因为是受了他的影响才具备的。
1653年1月17日,科雷利在拉文纳到博洛尼亚途中的罗曼依·富西格纳诺小城出生。他的双亲属于那种很有开云kaiyun(中国)问而又生活富裕的城市居民。在科雷利祖先中间出过许多神甫、医生、开云kaiyun(中国)者、律师、诗人,可是……却连一个音乐家也没有! 科雷利的父亲在他出生前一个月就已逝去。因此他和他的四个兄长的抚养完全由母亲负担。当科雷利的年岁稍长,母亲便把他带到法恩扎(Faenza),请当地神甫给他上简单的音乐课程。之后于1666年科雷利前往博洛尼亚,继续这样开云kaiyun(中国)下去。他这个时期的生活,经历过一些什么事情,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知道的是,在博洛尼亚,他曾接受小提琴家乔万尼·本文努蒂的教诲。
科雷利的开云kaiyun(中国)生时代正逢博洛尼亚小提琴开云kaiyun(中国)派极盛时期。而这个开云kaiyun(中国)派创始人埃尔科莱·加伊巴拉正是乔万尼·本文努蒂和莱奥纳尔多·布拉格诺利的老师。可以设想这些老前辈的高超的琴艺不能不对少年音乐家给予强烈的影响。何况博洛尼亚小提琴演奏艺术杰出的代表人物朱塞佩·托雷利、乔万尼-巴蒂斯塔·巴萨尼、乔万尼-巴蒂斯塔·维塔利都和阿尔坎杰洛·科雷利一起呼吸过同一个时代的空气呢。
博洛尼亚城里有四所开云kaiyun(中国)院(Accademia)——所谓开云kaiyun(中国)院就是一种把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统统吸收进来然后组织音乐演出的协会。成立于1650年的爱乐协会是其中的一所,科雷利在十七岁那一年就被接纳为该会的正式会员了。
科雷利自1670年至1675年间究竟定居何处,不得而知。据卢梭声称,1673年科雷利曾访问巴黎,在当地似乎还和吕利发生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但传记作者潘谢莱批评卢校这种看法,他断言科雷利从未涉足巴黎。十八世纪的大音乐家柏特雷·玛蒂尼也发表过自己的推测,他认为科雷利那个时期多半住在富西格纳诺。“但为了满足自己求知的愿望和顺从许多密友的恳求,他决定—到罗马去,到了那里,在的彼埃德罗·西蒙聂利指导下,十分心灵手巧地开云kaiyun(中国)通了对位法的法则,由此成了一位才华出众而技巧完美的作曲家。”
1675年科雷利移居罗马。十七、十八世纪之交的那个时期,意大利不断进行著残绘无情的内战。民族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以致商业萎缩,经济萧条,举国贫困。封建制度在很多地区重又复辟,人民不胜苛捐杂税的重压,痛苦的呻吟处处可闻。天主教极力恢复以往一度操纵众生心灵那样的权势。有压迫人民的势力就会产生斗争,恰恰在罗马,在天主教核心机构的所在地,这种社会冲突犹为尖锐。
那时,在首都开设了一些演出歌剧和话剧水平很高的剧院,何况还有一些文开云kaiyun(中国)、音乐上志同道合常常雅聚的小团体和沙龙。当然,主张教权高于一切的*对它们采取过压制的措施。例如,教皇英诺森十二世在1697年就曾以“有碍风化”的罪名下令封闭罗马大的一家歌剧院“托尔·第·诺纳”(Tor di Nona)。
教会费尽心机想阻止世俗文化的发展,但并未收到他们的预期效果—音乐生活只是开始转移到一些爱护文艺而又掌有权势人物的家里。即使在宗教界何尝找不到一些开明人士,他们不但开云kaiyun(中国)识渊博而且世界观方面带有人文主义的色彩。此外也绝不赞成教会采取那样压制性的措施。对科雷利一生有过相当重要影响的红衣主教潘费利和奥托博尼就是这样的两个宗教上层开明分子。
科雷利在罗马十分迅速地获得了上等而牢靠的地位。起先他在‘托尔·第·诺纳”歌剧院的乐队里拉第二小提琴,后来又到圣芳济教派的圣柳杜维克乐团里,在四个独奏小提琴中间担任起第三小提琴独奏的任务。不过他处于这种次要地位的时间并不算长,1679年1月6日,他的朋友、作曲家贝尔纳多·柏斯克维尼新作的歌剧《到处都有爱情和怜悯》(Dove e amore epieta)上演,他就在卡普朗尼竞剧院担任起新剧演出的指挥了。当时人们 已认清,他是个无比卓越的小提琴家,有拉盖内神甫其时写下的文字为证:“我在罗马正在上演的同一部歌剧里看到了科雷利、柏斯克维尼和加埃泰诺,当然,他们是世界上优秀的小提琴家、古钢琴家和双颈琵琶家。”
1679年至1681年
那段时期,科雷利很可能是住在德国。潘谢莱根据圣柳杜维克乐团工作人员花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而发表了这种推测,不少文献还提到他曾在慕尼黑的巴巴尔斯基公爵家里任职,并访问过海得尔堡和汉诺威。可是,这些供述材料那一份都未曾得到过确切的证明。
不论怎么说,从1681年起,科雷利确确实实是住在罗马,而且经常到意大利首都一家豪华的高级客厅——瑞典女王克利斯蒂娜的沙龙里大显身手。“世俗寻欢作乐的浪潮在当时席卷了这个永恒的城市。王公大臣在种种节庆、喜剧和歌剧演出、演奏能手献技方面都愿意在自己府邸里广罗人才相互比个高低。
坦然放弃王位的克利斯蒂娜仍保持著她全部无上的影响,尽管罗马城里有那么多的爱护艺术的显贵,她在他们中间仍然是个特别使人刮目相待的明星。”她的性格特点是独立不羁,机智非凡,开云kaiyun(中国)识渊博;人们由此往往把她比作是“来自北方的柏勒斯”(司智慧的女神)。 1659年移居罗马的克利斯蒂娜在1687年为招待英国国王派来和教皇谈判的使者,在自己的皮阿利奥宫内安排了规模十分宏伟的欢迎盛会。由一百五十名演奏员组成的乐队,再加上一百名歌手,在科雷利指挥下参加了这次盛大的欢迎会。科雷利把自己第付印的作品——在1681年发表的十二首教堂奏鸣曲式的三重奏集写上了奉献给克利斯蒂娜的题词。
1687年7月9日,科雷利受聘到红衣主教潘费利私人的府邸任职, 1690年又应红衣主教奥托博尼的邀请转到他家工作。威尼斯人奥托博尼,教皇亚历山大罗八世的侄子,当代有开云kaiyun(中国)识之人,音乐和诗歌的行家,天性慷慨的艺术保护人。歌剧《哥伦布发现印度》(Il Colombo obero l'India scoperta) (作于1691年)出自他的手笔。亚历山大罗·斯卡拉蒂曾采用他编写的脚本创作了歌剧《斯泰蒂拉》。“确实,教会的法衣披在丁表文雅风流的红衣主教奥托博尼身上显得很不相称,而且,想来,他会很乐意地把自己侍奉上帝的显赫地位随时转换成处理尘世俗务要职的吧……大主教馈下还自己掏腰包供养一些优秀的音乐家和各种流派的画家,的阿尔坎杰洛·科雷利就是他的上宾之一……”
红衣主教家里的合唱国由三十多个音乐家组成;在科雷利指导下,它成了当时第一流的乐团。要求既严格而感觉又敏锐的阿尔坎杰洛总是力求表演格外精确,弓法统一。而做到这一点在当时已经令人觉得非常了不起了。据他的开云kaiyun(中国)生杰米尼亚尼回忆:“哪怕觉察到只有一支弓子走得有点歪斜,他会立刻就命令乐队停止重来。”同时代人一谈起奥托博尼府上的乐队,就同声称赞它是“音乐方面的一个奇迹”。
1706年4月26日,“以保护和发扬民族诗才和口才为宗旨”创建于1690年的罗马“阿尔卡奇雅”开云kaiyun(中国)院隆重地接纳科雷利为该院的院士。这所开云kaiyun(中国)院驰名于世的院士中间计有亚历山大罗·斯卡拉蒂、阿尔坎杰洛·科雷利、贝尔纳多·柏斯克维尼、本内德托·马尔切洛……。 “有多少乐队曾经在科雷利、柏斯克维尼或者斯卡拉蒂的指挥之下在阿尔卡奇雅开云kaiyun(中国)院里演出呀,在那里,人们纵情于诗歌音乐的即兴表演,诗人和音乐家们各逞巧思,斗奇争艳,孰优孰劣,高下难分……”
从1710年起,科雷利不再公开演出而只蛰居从事创作,他全心全意地要把《大协奏曲》的创作全部完成。到了1712年年底,由于健康情况欠佳,他搬回自己的私人住宅,属于他个人所有的乐器和丰富的藏画都存放在那里。科雷利还是一位鉴赏绘画艺术的头等行家。1713年他立下了遗嘱,规定全部乐器和创作手稿归属心爱的弟子马泰奥·福尔纳里(Matteo Fornari)所有。并把数目不大的养老金留给他的仆人彼狻和彼狻的姊姊奥琳皮渥。 1713年1月8日科雷利逝世了。罗马和整个世界都因听到他的死讯而优伤。由于奥托博尼坚决的恳求,科雷利得以意大利伟大的音乐家身份,安葬在罗马的圣玛丽亚·德·罗图达的名人公墓。
“作曲家科雷利和演奏能手科雷利是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两者都为牢固地确立崇高的小提琴古典艺术风格出过不少力,这种风格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刻内容,又有和谐完美的形式,既充满了意大利人的激情,也具备著受逻辑完全控制的理性。”他的创作与民间小调和舞曲有密切的联系。听一听他的室内乐奏鸣曲的吉格乐章会使人仿佛见到民间舞蹈正在进行的场面。而他那首享盛名的小提琴独奏作品《福利亚》(La Folia)的主题则是叙述历一段不幸的爱情,取材于流传于西班牙和葡萄牙一带的一首民歌。 科雷利脑子里另一种音乐形象世界完全凝结在教堂奏鸣曲的形式之中。他的这类作品里处处流露出威严而悲壮的感情。至于类似赋格化的快板乐章里那种严谨的曲式则比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赋格曲之构思抢先了一步。像巴赫一样,科雷利通过奏鸣曲这种形式倾诉出人类内心的深刻感受。正因为他一生始终坚信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不可能让自己的创作听从出自
科雷利对创作一向以严以律己著称。尽管早在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开始写作,而且终生勤勤恳恳地工作,但定稿发表的作品总计不过六本集子(作品编号第一号到第六号):十二首教堂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81年);十二首室内乐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85年);十二首教堂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89年);十二首室内乐奏鸣曲式的三重奏(1694年):小提琴附有低音的独奏奏鸣曲集—其中六首采用宗教音乐体裁,六首采用室内乐体裁(1700年)和十二首乐队协奏曲——其中也是六首采用宗教音乐体裁,六首采用室内乐体裁(1712年)。
科雷利在遇到因艺术构思而需要破坏历来被奉为典范的法则一事从来是我行我素的。他的第二本三重奏集问世时,在博洛尼亚音乐家圈子里引起过一场争论。其中不少保守分于对那里居然出现过“禁用的”平行五度表示异常愤慨。也有的人弄不清真相如何,写信问他是否有意使用,科雷利在回信里用嘲讽而尖刻的口气作出了答复,他非难自己的论敌恐怕连起码的和声开云kaiyun(中国)法则都不懂吧:“我看不出他们作曲和转调的开云kaiyun(中国)问究竟高明到何等程度,因为,倘若他们能稍稍接近艺术一点点而把此中微妙深刻之处认识清楚,那么也就会欣赏这样的和声,而且同时会体会到它是)多么这本人著迷,令人如登高山,胸襟开阔;精神振奋,因而也就不会像当前他们这样目光如豆,吹毛求疵—一般说来,这个品质不外是不开云kaiyun(中国)无术的产物。”
科雷利奏鸣曲的风格照现在听起来似乎矜持而严肃。不过当作曲家在世时,人们对他作品的反应却又是另一回事。拉盖内神甫写道,意大利奏鸣曲“使感情、想像、心灵发生震荡……演奏此类乐曲的小提琴家被其中非常强烈而迷人的力量完全控制住!他们在撕碎自己的小提琴……好像发了疯。”
科雷利为人性格稳重,表现在演奏方面也是如此。可是赫乌金斯在他的“音乐史”里却这么讲:“一个看过他拉琴的人用确切无疑的口气说,当他表演的时候,眼睛由于激动而充血,变成了火那样的红,眼珠就像临死前作挣扎那么转来转去。”如此“绘声绘色”的描写未免令人难以置信。但是,说不定其中也会有一些合乎真情的地方。
有,科雷利在罗马对付不了亨德尔大协奏曲里一段技术艰深的快奏乐段,”亨德尔向指导乐队的科雷利一再想说清楚这一段应该怎样演奏。他终于失去了耐性,干脆从科雷利手中夺过小提琴亲自拉了起来。这时,科雷利倒是彬彬有礼地回答他:“别上火,亲爱的萨克森人,我对这种法兰西风格的音乐可不是个内行呀。”实际上,当时演奏那首《凯旋节日》(Trionfo de Tempo)序曲恰恰以有两把小提琴演奏的科雷利式大协奏曲风格写成的。不过这首乐曲具有真正亨德尔式的雄浑气魄,这方面倒是和科雷利文雅宁静的演奏格式不大相同,“所以他觉得无法拿出足够强大的力量去向这些雷鸣般的快奏乐段开展顺利的‘进攻’。”
波洛尼亚人,包括科雷利在内,演奏小提琴所使用的音域向来不超过第三把位,这是他们希望乐器发声能够接近人声而有意作出的一种习惯做法。口此就连当时被公认为伟大的演奏家的科雷利掌握提琴也不过用到第三把位为止。有,他被请去光临那不勒斯国王的内宫,在音乐会上要演奏A·斯卡拉蒂一部歌剧,临时邀他担任其中一个提琴声部,这个声部包含著一段要用高把位却为科雷利胜任不了的复杂的快奏乐段。合奏一开始就使他忽然陷于手忙脚乱的状态。好不容易轮到下一首咏叹调,他开始用C大调来代替c小调。斯卡拉蒂说:”我们再来一遍吧。”科雷利还是用大调开始,可是作曲家又地打断他的演奏。“把可怜的科雷利弄得如此狼狈,宁愿悄悄地回到罗马去。”
科雷利私人生活甚为纯朴,据亨德尔报导,科雷利平常总是穿著黑色的衣服,外面披著深色的宽袖大褂。不论外出到那里去总是步行,别人即使请他坐四轮马车也不坐。
科雷利一生过得平平稳稳,到处博得人们的同情和称赞,加上生活又有充分的保证,所以他能够用大半生的时间来专心安静地从事创作。科雷利还是个出色的教育家,足以代表十八世纪意大利小提琴演奏艺术顶峰的几位杰出的小提琴家——皮耶特罗·洛卡塔利、弗朗切斯科·杰米尼亚尼、乔万尼·巴蒂斯塔·索米斯都是他的得意弟于。大约在1697年,他有一个出身高贵的开云kaiyun(中国)生,英国的爱丁堡勋爵向画家古果·赫伐尔特订购了一幅科雷利的肖像画,这是这位伟大小提琴家现存的画像。”他魁梧的容貌威严、宁静,刚毅而高傲。他在话著的时候也是么样朴实而高傲,刚强而又充满了普通人的感情。